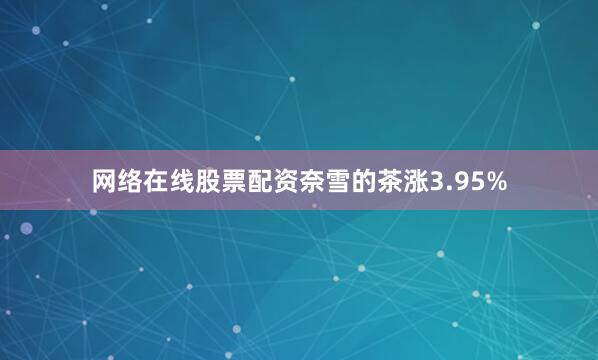近读刘禹锡,常常会在读到有关的章节想起杨慎,总感觉他们两个虽相隔近千年,却有着某种特别相似的地方,尤其是他们两个的效忠君王的执念。刘禹锡与杨慎的“忠君”,就像两株被狂风扭折的苍松古柏——根须深扎于“致君尧舜”的沃土,枝干却被皇权的雷霆劈得焦黑,终其一生在“欲济无舟楫”的困顿里,挣出几分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孤光。
图片
刘禹锡的忠,是“衣带渐宽终不悔”的执拗。永贞革新失败后,他被贬朗州司马,诏书里“纵逢恩赦,不在量移之限”的字眼,像一道无形的枷锁,锁死了他二十三年的归途。可他在《朗州窦常员外寄刘二十八诗见促行骑走笔酬赠》里写“明时久不达,弃置与君同”,将自己的沉沦与友人并论,字间却藏着“君恩未报”的隐痛。元和十年被召回京,他路过玄都观,忍不住吟“玄都观里桃千树,尽是刘郎去后栽”——那满观桃树,分明是新贵们的得意嘴脸,而他这株“病树”,偏要在花丛里透出不屈的枝桠。宪宗震怒(刘在顺宗时期,追随权臣王叔文,是改革的干将,但顺宗禅让,宪宗继位,他们变成了新皇帝不能容纳的旧臣),再度将他贬往更远的连州,仿佛在说:“这颗忠心,朕消受不起。”可他到了连州,仍“重其土风,作《竹枝词》十余篇”,把巴楚的俚语唱成诗,骨子里还是那个“愿陛下法太宗”的谏臣。直到晚年,他在洛阳写《酬乐天咏老见示》,说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”,那霞光里,何尝没有对“君恩再顾”的最后一丝期盼?就像屈原在汨罗江畔“眷顾楚国,系心怀王”,明知“信而见疑,忠而被谤”,仍要“上下而求索”。刘禹锡忠君思想在诗歌创作中也特别明显,他强调应该“致君及物”,致君,就是要对皇帝表达忠诚,就是要讲政治,要有高度,体现觉悟。及物,就是要深入实际,触及事物本质,就是有深度,反映生活。所以他的文学主张就是这样的,他不可能不表达!他也不会乱表达,更不会大逆不道的表达,你看看他所有流放生涯诗歌中的文字,没有一句骂皇帝骂朝廷的话,骂小人、讽刺得势张狂之徒的不少。其实,这不妨碍他采用独特的视角,就自己有把握的题裁,大胆说真话,把真话说透说实在!
图片
杨慎的忠,则是“伏清白以死直”的刚烈。“大礼议”之争中,他率百官伏阙哭谏,声震宫阙:“国家养士百五十年,仗义死节,正在今日!”嘉靖帝的廷杖落在身上,血肉模糊间,他未发一语求饶,倒像西汉的晁错,明知“削藩”会招杀身之祸,仍要“为国远虑”。流放云南途中,他过金沙江,写下“江声月色那堪说,肠断金沙万里楼”,那断肠处,是“君恩断绝”的锥心之痛。当在蛮荒之地陷入绝境,随行的仆从劝他:“老爷,不如寻个机会逃吧。” 他只是摇头,指着天边的北斗:“君恩如北斗,臣心似北辰,纵九死其犹未悔。”嘉靖皇帝的恩赦令一次次下达,因“永不叙用”的诏书,却总把 “杨慎” 的名字刻意抹去。有人劝他向皇帝低头认个错,他却指着案头的《春秋》:“宁可抱香枝上老,不随黄叶舞秋风。”抵达永昌的那天,他站在破败的卫所门前,看着墙上 “忠孝节义” 四个褪色的大字,突然想起父亲杨廷和当年的教诲:“文死谏,武死战,此乃吾家风骨。” 那一刻,所有的伤痛与愤懑都化作了一声长叹,融进了滇西的夜风里。可他在永昌卫的茅屋里,仍校勘《文心雕龙》,批注《史记》,仿佛要把对朝堂的忠,化作对文脉的守。嘉靖帝晚年常问“杨慎安在”,臣下答“老病”,——这位君王像极了汉武帝对李陵,明知其忠,却偏要让他“身在匈奴心在汉”,任其在蛮荒里枯萎。杨慎临终前写“万里滇云寄客愁,归期无定更添忧”,那乡愁里裹着的,是“生为大明臣,死为大明鬼”的执念,恰似苏武持节北海十九年,节旄落尽,初心未改。
图片
他们的悲剧,原是中国士大夫的宿命寓言。孔子周游列国而“道不行”,孟子见梁惠王而“迂远而阔于事情”,刘禹锡与杨慎不过是重复着先贤的轨迹——把“忠君”刻进骨髓,却撞上君王“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”的猜忌。刘禹锡的“沉舟侧畔千帆过”,是看清了“君恩如流水,既往不可复”的通透;杨慎的“是非成败转头空”,是参透了“帝王心术,本无定准”的苍凉。可即便如此,他们仍在贬谪之地播撒文化的火种:刘禹锡在夔州教民种稻,杨慎在云南讲学授徒,仿佛在说:“君不用我,我便用我之忠,泽被一方。”
图片
这让我想起屈原的《离骚》: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。”刘禹锡与杨慎的“忠”,从来不是对帝王的依附,而是对“道”的坚守。君王的“永不叙用”,不过是给他们的生命,镀上了一层悲壮的金辉——就像被狂风折断的古柏,虽不能参天,却在断裂处,生出更倔强的新枝,直指苍穹。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
杜德配资-配资公司10大排名-配资加杠杆-配资专业炒股配资门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